《最蓝的眼睛》
作者:托尼·莫里森 评价:⭐⭐⭐⭐⭐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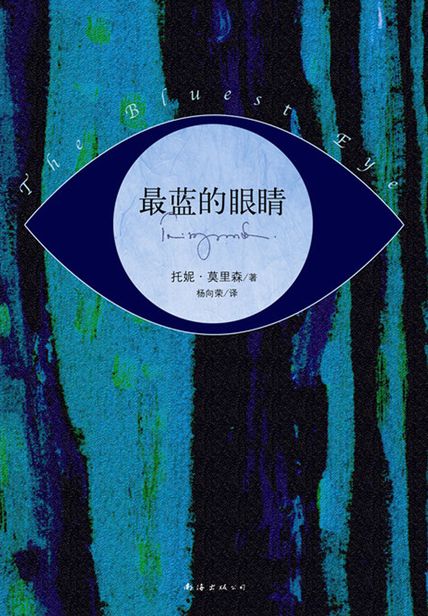
出版社: 南海出版公司 原作名: The Bluest Eye 译者: 杨向荣 出版年: 2013-8 页数: 227 定价: 32.00 ISBN: 9787544257206
不愧是诺奖得主,开头就非常厉害,我对这本书的兴趣全都来自开头,而后更是欲罢不能,两天内看完。
千万别声张,一九四一年的秋季,金盏花没有发芽。当时,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。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,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,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。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。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,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: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,种子就会发芽开花,一切都会没事的。 很久以后,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。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,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。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:是我的过错,我把种子埋得太深。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。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,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。我们的天真、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,颗粒无收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,所有那些希望、恐惧、情欲、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,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。乔利·布里德洛夫死了,我们的纯真也死了。种子枯死了,她的孩子也死了。
故事并不复杂,佩科拉一家被认为是最丑的人,当地金发碧眼的审美让她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,早产而孩子夭折后,她陷入自己的臆想世界,得到了那双蓝眼睛。
故事从秋天开始,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在秋天认识亨利先生和佩科拉。两个家庭共享黑人的痛苦,但又因细微的差别而分道扬镳。姐妹花的生活就像佩科拉的对照组,区别在于他们父母,姐妹花父母得知亨利对弗里达的猥亵,又打又骂,举枪把人活活吓跑。佩科拉的妈妈得知时,没有相信。最终是父亲发现她怀孕后,自己逃跑了。
主视角的转换让故事穿插了几个长辈的故事,于是每个人都跳出来,活灵活现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宝琳,佩科拉的妈妈,一个跛脚的阿拉巴马州人,残疾人,所以别人不欺辱她,但也不靠近她。很小她就习惯欣赏独处,她无法改变身体的乱序,但热衷于恢复外物的秩序。“井井有条”是她心灵的舒适圈,秩序让她安宁。也因此,她喜欢数学。如果在一个不同的年代,她或许能深入研究数学的序列,而不是守着调料盒、刀叉的分类。
当然,最悲哀的是,她和乔利曾真心相爱过。
我想告诉你,当我第一次看到乔利,那感觉就像故乡的那次体验,各种颜色搅在一块儿:那是在一次葬礼之后,我们所有孩子去捡浆果,我把几只果子放在星期天穿的衣服口袋里,果子挤烂了,染了我的屁股。整条裙子都染成了紫色,再也洗不掉。我和裙子都是。我能感到紫色深深地扎进我的体内。还有爸爸从田里干活回来后妈妈做的柠檬水。冰凉凉黄澄澄的,靠近瓶底还漂着些柠檬籽。还有我们离开家乡那晚金甲虫在树丛里发出的道道绿光。所有这些色彩都沉淀在我的体内。当乔利走过来挠我的脚时,那感觉就像浆果、柠檬水、金甲虫的绿光,各种颜色全都搅在一块儿。那时乔利还很瘦,眼睛真的很亮。他经常吹口哨,每当我听到他的口哨声,身体就会忍不住战栗起来。
生活并没有因为相爱而更好,只会因为生活的糟糕而磨灭爱情。在忍受中,宝琳生下了两个孩子。在怀孕时,她对孩子是那么期待,经常自言自语对肚子说话,让人不由得幻想一个有爱的母亲,一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。
他离开后又来了几个医生。一个老一点,其他几个挺年轻的。老一点的那个给年轻的指点生孩子的事。给他们示范如何操作。他走到我跟前时说,给这些女人接生不会有任何麻烦。她们能很快生出来,而且不会疼痛。就像下马驹儿一样。那几个年轻人低声笑了笑。
我跟白种女人一样会觉得疼痛。不要因为我以前没有扭动没有叫唤就认为我没有疼痛感。他们是怎么想的?难道因为我知道如何在生产时不叫不闹,我的屁股就不会像她们一样撕扯和疼痛吗?再说,那个医生根本就是一派胡言。他肯定没见过母马。谁说母马不知道疼痛?就是因为母马不会叫出声来吗?就是因为它不会说话,他们就以为那不疼吗?如果他们仔细看过母马的眼睛,看见眼珠子朝后翻着,看见那痛苦的表情,就什么都知道了。
两个孩子的花费让她不得继续外出工作,在一个富贵的白人家庭里,她找到了自己梦想的家的样子。
她在瓷盆里给费舍尔家的小女儿洗澡时,银色水龙头里温热清澈的水流个不停。她用柔软的白毛巾把孩子的身子擦干,套上柔软的睡衣,然后开始梳理孩子金黄的头发,享受着发卷在手指间滑动的感觉。再也没有锌皮浴盆,没有一桶桶在炉子上烧好的水,没有在厨房水池里洗过、在尘土飞扬的后院里晒干的又脆又硬的灰扑扑的毛巾,没有粗硬如羊毛般又黑又乱的头发了。
一天结束时,站在厨房里欣赏自己的手工杰作简直成为她的一种享受。她知道橱柜里有成打的香皂、成包的火腿,还有锃亮的锅碗、干净的地面。耳边听着:“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她走的。像宝琳这样的人我们再也找不到了。她一定会把一切都弄得井井有条了才离开厨房。说实话,她就是最理想的仆人。”
最理想的仆人。
乔利的人生也不全是黑暗,就像宝琳记忆深处的金甲虫光芒、紫色浆果、黄澄澄的柠檬水,乔利也有,那是和布鲁一起吃西瓜的记忆。对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来说,布鲁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父亲的身份。
还记得某年七月四日的教堂野餐上,有一家人准备破西瓜。几个孩子围成一圈观看。
会做出那种姿态的一定是魔鬼——把世界抓在手中,随时准备摔在地上,把里面甜蜜、温热的红色瓜瓤摔出来让黑人分食。
布鲁跳了起来。“哦……哦,”他低声呻吟,“瓜心崩到那儿了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既惋惜又开心。大家一起朝那一大块既不连皮又少籽的瓜心望去。瓜心滚到布鲁脚边不远的地方。他弯腰捡了起来。血一般红,断面结实,看着很甜嫩,边缘饱含汁液。他太过明显甚至有点下流地沉浸在它许诺的愉悦中。 “吃吧,布鲁,”那位爸爸大笑着说,“你拿着吧。” 布鲁微笑着走开了。孩子们在地上乱跑着找碎西瓜。女人们给那些最小的孩子抠出瓜子来,同时给自己掰下小块尝尝。布鲁和乔利的目光相遇了。他向乔利招了招手。“过来,孩子,咱们俩来吃瓜心吧。” 一老一少坐在草坪上分享着瓜心。这是地球最甜蜜的内脏。
然而,他并不知道父母该如何对待孩子,他就没有受过这种对待,因此对自己的孩子也不管不顾,无法理解、无法处理亲子关系。也许正是这种剥离,让他即使理智上知道他们是父女,情感上却不当女儿看待。是女儿吗?除了一个身份,一声呼唤,他什么都没给过她。而在醉酒的幻想中,他却把种子撒向自己的黑土地。
还有那个牧师,一个狡辩的柏拉图同性恋+恋童癖。也是个被白人文化逼疯的人,家族每一代都要以白人为首,越来越多的人和白人联姻,则他们血液里白人的浓度就会越高。被父亲赶走后,他用骗人的伎俩赚钱,用糖换取女孩们的使用权。他与来求取蓝眼睛的佩科拉感同身受,但仍利用她除去自己厌恶的一条老狗。用圣洁伟大掩饰自己的卑劣。
故事在夏天结束。贯穿人生四季。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家的事了,然而谈话内容从不因时间而改变。以前如此,现在如此。
“唉,他们应该让那女孩退学。” “是应该。她多少也有点过错。” “哦,拜托。她只有十二岁。” “是吗?谁知道呢。她怎么不反抗?” “也许她反抗了。” “是吗?谁知道呢。”
有韵律的文笔,跳跃的时空,值得欣赏的写作手法,不过有些人也许会混乱而不悦。我给5星,但太苦难的生活,应该不会再看第二遍了。